ͮ�ܓP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`������Ů�ԕ���
1990��10��20����һ���}�顰Ԋ���c����Ů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ӑ���ڼ��ݴ�W��ɼ����У�e�����@��Ӣ�Z�W���Pע����Ů���ČW���Ԅe�Ļ����о������R��һ�ã����hՓ�ĺ���Ԍ�̖����ʽ���l(f��)��Ӣ���ڿ�����ʷ���}����1992���13�ڣ����錣̖�������ԡ��ĝh�W���M�b��Charlotte Furth��ָ�����@һ���}���о�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όӋDŮ���ČW��Ʒ����Ҋ���ա���recovery�������@Щ�ŵ�Ԋ�~���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罻�����ṩ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ͬ����1990�꣬���ô��A��W�߷��㝍��Grace Fong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δ��~�W���h�ψ���ˡ�Փ�~���Ԅe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ǡ�һ�ģ�Ӣ�İ�1994�������g��2003�꣩���о��~��Ώ�����ҕ���D�Ƶ�Ů�������Ĵ��_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픵(sh��)ʮ����о�����Ů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顶��Խ�|�T������Ů������Փ����Ӣ�İ�2010�������g��2014�꣩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ġ��w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㝍�J�����Ժ��Ŀ���1901�C1988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ć��Ȍ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Ŵ��DŮ�����M���^ϵ�y(t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˸��_�е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DŮ�����ں����ǽ�(j��ng)�v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°l(f��)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rediscovery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
�M�܃�λ�W�ߵIJ�ͬ���~�ڃȺ��ϲ��]�Ќ��|�Եą^(q��)�e�������ڷ��㝍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����D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@Ȼ�h�ǃH���ڞ鼮���o���IJ�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Ǟ��@ЩŮ�ԵIJŌW���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P�ĵ���Ů���ı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N�����ںܴ�̶�����ֻ�Ќ�Ů���Լ�ӛ��µ�������˼�w�Լ��H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ҕ�����п��ܽ☋�ǷN�^�ں��λ��ij�Ҋ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һ�N��ͬ�ڼ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J�R����ʾ���Ї�����c�Ļ���(j��ng)���ď��s���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Խ�|�T�����3���@�N���{�����°l(f��)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˼·�����w�F(xi��n)�ڷ��ϵČ������䱾���ߣ�����Ů�Ե��Ԅe�������܄����w���Č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Q���䱾���ߡ���Ӣ�İ�2008�������g��2024�꣩��ԓ����ʿ���A�ӵ�Ů��Ԋ�ļ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Ĺ�(ji��)�D�Ԃ���檋D��(chu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Õ������ČW�uՓ�c���@�Ă����}��̽ӑ�ČW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Ů�Ե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ߌ�Ů�ԕ���ҕ��һ�N�Ļ����`��ʽ�����D�U��Ů�Ԅ�(chu��ng)�����\�ЙC�ƣ��|���ı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ؑ��ČW�о��ġ��Ļ��D��څ�ݡ�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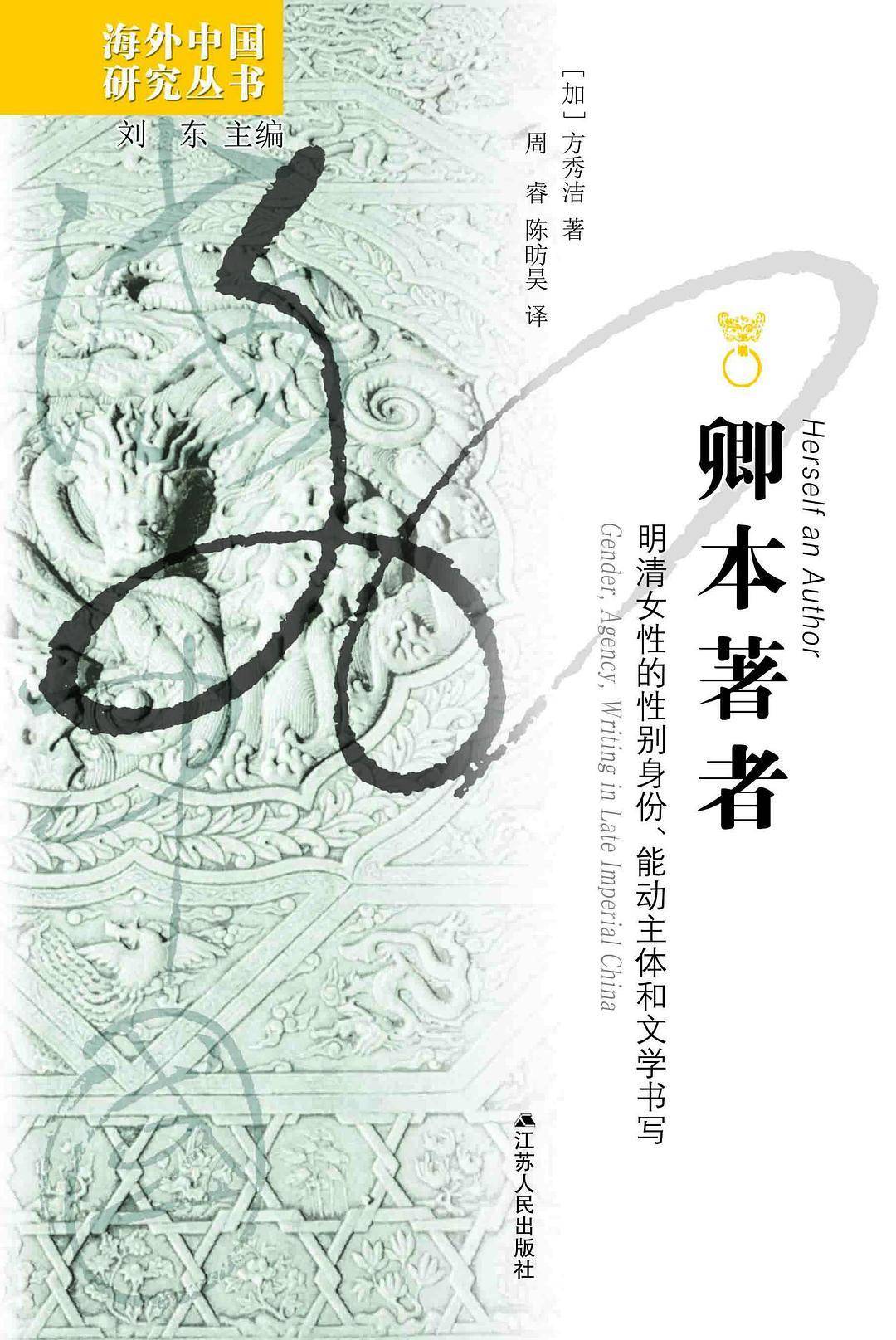
һ��Ů�����c�܄����w
���F(xi��n)�ڡ��䱾���ߡ�Ӣ�ĕ�������P�I�~���܄��ԡ���agency��؞����ȫ����Ů�����ߵ��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܄��ԡ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顰�����ԡ�/�����w�ԡ�/�����w�ԡ���ָ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ȡ�Єӵ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U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}����Ů����Ҏ(g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Ԅe�����Ќ���ͬ���ݵ����ұ���/�٬F(xi��n)��self-representation�����@һ�h�}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ݵġ����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еġ�author�����cŮ�������п̮������˹����䡱/�����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еġ�herself�����^(q��)���_����ǰ�ߏ��{����Ů�Ե��ı����`�����ߏ��{����Ů�Խ�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N�^(q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ČW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y(t��ng)�rֵ�wϵ�С������x�ࡱ��self-empowerment����Ŭ���c�ׅf(xi��)ͬ��չ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ӑ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\���@һ����֮ǰ���б�Ҫ���˽���W�g��·��
��С�s�ڡ�Ů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W�о�����Ů��Ԋ�����Փ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2013�꣩һ�������ᵽ����Ů�����x�ČW���u�ͺ�Y�����x��Փ��Ӱ푣�ָ���vʷ�İl(f��)չ���ČW�Ą�(chu��ng)���߽��ˌ��ڡ��܄��ԡ���ͬ��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O����Ҳ�S���˲�����ȫÓ�x���R�ΑB(t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Ԓ�Z�������Z�ԵĹ����Ժ��_���ԣ��Լ����R�ΑB(t��i)�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ʹ�������ڸ��N���w֮�g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ƵĿ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\�����N����Ԓ�Z��☋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N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Ů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15����ָ������Ů���ČW�顰�܄��ԡ���Փ�ṩ��һ�����w�Ěvʷ�Ļ��Z�����e�ǿ��]����ҵ��Ԅe�����Լ��c֮���P��Ů���P�����ߙ�Ľ��]���ڴ��Z����̽ӑŮ�Խ�(j��ng)�����г�Ч���^���Ԅe���Ӱ��ČW��(chu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u���`���M�����M�ČW������Ԅe�Ļ��о����°l(f��)�F(xi��n)��
�ČW�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aureen Robertson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_��(chu��ng)֮�����佛(j��ng)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׃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Ԋ�е��Ԅe�����ҕ�������Changing the Subject: Gender and Self-inion in Authors�� Prefaces and ��Shi�� Poetry, 1997����Ů��Ԋ�˵������٬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(q��)����Ů��Ԋ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ݵIJ�ͬ�ӴΣ�һ�Ǵ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ı�֮��Ĭ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е�Ԋ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ݵ����߽�ɫ��ͨ�������l(f��)��һ���ı��е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Ԋ���И����ĸ��N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С�s�J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»ؑ���Ů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ε���Փ�����w�U��Ů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e�C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�ʾŮ��ͨ�^�ČW�Č��c�l(f��)��չ�F(xi��n)�e�O�Ą�(chu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
ͬ�������o90�����ʷ�W�猦�Ї�Ů�Ե��о�Ҳ�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ƌW�Ć��l(f��)���M��̽���܄����w�h�}�������ԌW�߸ߏ��U��Dorothy K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h֮�����|�ӎ�����ĩ������ϵIJ�Ů�Ļ�����Ӣ�İ�1994�������g��2004�꣩�н��b��W��Jane Monnig Atkinson��˼·���á��p���c���vʷҕ�ǣ������y(t��ng)�r�ڵ�Ů��ҕ�顰�ܺ��ߡ��c���܄��ߡ���agent���ĽY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Ԓ�Zҕ���y(t��ng)���Ů�ԃH�H�����ܺ��ߵĿ̰�ӡ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ģ����Ů�ԵČ��`��ӡ�Ů�Ե������J�R�@���ؾS�������ӵ��U�Ů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ڴ������{�m��ĥ�ϵĚvʷ����ֵ��ע����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˭���˹���أ�Joan Scott��Ӱ����h���Ԅe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17���o��ĩ����Z���µġ�Ҏ(g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ҽ�(j��ng)���c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���c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H���wϵ������ƶȣ��͡����^�Jͬ��/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ݡ�����ӳ��Ů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g�ĄӑB(t��i)�Pϵ��
�ߏ��U�J�飬�ČW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֮�Hʿ����ͥ��Ů��Ԋ�˳�Խ�����ڼ������̎�r���ĸ���V響��g��һ�N�������@ЩŮ�����ܵ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(f��)�ĸ�����ӽ�ͬ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ǵ��·����нK�����ڃ�����ٳּ҄յ�Ů�Կ�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ЩŮ�Ե����w���ݑ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Աȼ�ijɾͣ������ČW��(chu��ng)����֮�Ё����⣬���w��ӳ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Ե����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͂��ڕ�����ˇ����Ը���Ą�־Ȥ��ͬ��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ˇ�g�b�p�����ȷ������M���@Щ�О顢־�������ͻ���˂��y(t��ng)���Ԅe��ɫ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y(t��ng)�W�f������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y(t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ӽӼ{�;S�o������ܵ���ҶY�̵�Ĭ�S��
����Ů�ԡ����w���ݡ����о�֮���Գɞ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Ҏ(gu��)ģ�@����Ů��Ԋ�ļ��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ض���Susan Mann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Y��䛣�ʮ�����o����ǰ����Ї��DŮ����Ӣ�İ�1997�������g��2004�꣩�ᵽ�ģ���Ů���ı��{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ԡ��^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Ҏ(gu��)��ռ��(j��)�y(t��ng)�ε�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Ŀ�еărֵ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Y��䛡����4�����@�N�о�ȡ������Ů�����ߵ��܄����w�h�}�ɞ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ԡ��䱾���ߡ��ڶ��¡���߅�������ģ�檋D���ČW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߾۽��㽭ƽ���@��֮��ꑟ@֮���ʣ�1752��C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�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ھ���ʵĄ�(chu��ng)����Ͷ��Ă��y(t��ng)�Y���⺭��檋D�ڶY���ϵ�߅���Čٵ�λ��ʹ�䡰����б��_�ϔ[ÓŮ�ӹ�혱��t�����y(t��ng)���`�rҲ�Ʊ����ҵ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硱���83����ʹ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ʹ��ɞ��^��Ů�����ߡ��܄��ԡ�������λ����
�cҪô��Ӌ��D��Ҫô�⼵�ܺ��Ŀ̰弧�����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Ǽ����гʬ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ǵ�����̎����ֶ��Ǻ������H�ܵ���ꑟ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ؑ�[ָ�c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ֵĮ��棬������(li��n)�뵽��ĸ�nŮ�Ĉ�������ꑟ@�x�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˄t�˴������ꑼҵ�Ԋ���Շ��c��м~������ʵĄ�(chu��ng)���ṩ�ˌ��ɵĭh(hu��n)�����Ą����䌦���|���w��Ԋ��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܉����p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Ͳ�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ČW�Z�ԣ��硰���ꡱ�������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硰��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أ���đ�ر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Ů����c���w�T������߀ֱ���ڡ����ա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~�����@Щ���ɞ��������٬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Ȼ��Ȼ�،�Ů�ԏı��ӵ���ɫ���w�D׃?y��u)���Ԋ�����ӱ��_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ߵ����߀�H�ԅ��c�����ļ��ľ������棬Ҳ��Ԋ���uՓ�������M����Փ�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Ԅe�͵�λ�ڶY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о��ڲ�����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ڼ�ͥ�ɆT��֧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ČW��ˇ�g�u�������ֳɞ�����Ԅe����e�ߏ��Ե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˸ߏ��U���ڂ��y(t��ng)Ů���Ԅ�(chu��ng)��ͻ�Ƃ��y(t��ng)�Ԅe��ɫ���^�졣
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е����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ã���܇;İ�е�Ů�ӡ�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س������棨���C1645����檋D����1616�C1685�����܄��Եı��_�t�[�ö�����ͬ����̎�|�w����ʣ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ڸ��N�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Ԋ������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ߵĽ�(j��ng)�v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Ů�ԕ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Ԋ���y(t��ng)�Ѕf(xi��)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Ă��w���ݡ����142�����@ЩԊ����Ư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�;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µ��Ļ����g��Ҳ�S�Ǟ����@�N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в����Ɖ������]����Ԋ����ֱ������;�������y���܂���ӛ������ǽ����S���ˣ�1610�C1695���Ă�ӛʹ�Ƕ��U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֪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ʩ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Ó�ڄ�ʎ�ĕr�����mȻ檋D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ʺ�����ĕ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ͬ�����ǃ��߶��{��Ԋ�����}���Z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y(t��ng)�|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ͬ��Ů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ͬ�r����ꑟ@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@Щ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ڲ�ͬ�̶��Ͻ��뵽�DŮ�܄��Եı��_֮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Ů���Ļ��c�Ԅe���R
���܄���ӑՓ�Ļ�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䱾���ߡ�һ����չ�ˌW�猦����Ů���Ļ���ӑՓ���e�ǵ����¡��Ԅe�c��x��Ů��Ԋ�����u�еķ�ʽ�����o��Ⱥ�w�����漰��Ů�Թ�ͬ�w�h�}���ڱ�������֮ǰ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ߏ��U�����ض����e��κ��ɏ�ѽ�(j��ng)���о����|��Ů�Ե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㝍�Mһ��ָ��Ů��ͨ�^�����uՓ��ӣ��܉�Ů�Ե�Ԓ�Z���g���D����һ���˴˻�(li��n)��ͨ�����_�����ض�Ů��ָ���ČW�^�c�Ĺ���Ⱥ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152�����քe������ÿλŮ�Ը��Ԃ��صľ����ԣ������ޣ�1590�C1635���ġ�����˼����Ҫ���]����Ԋ�������漰���cŮԊ�˵�˽�˹�����Ԋ�������u�b�p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1614�C1683���ġ��|�㼯���Խ̌���Ů�pԊ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ȡ���u�b֮�£����t�d֮��ƷՓ���W�L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ߌ�Ԋ���ČW�rֵ���Pע�������磨1621�C�s1680���ġ�����Ԋ�����ṩ��ֹԊ����߀����Ԋ�˂�����ƽ���ԣ��@���»��{�����ƌ���1808�C1862���ġ�����ԊԒ����ǰ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֮�����ͨ�^�ʬF(xi��n)ŮԊ��֮�g���Pϵ�W(w��ng)�j������Ů���ČW��ͬ�w��ͨ�^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IJ�Ů��Ԋ�x�uע����ʽ�c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㝍�ʬF(xi��n)Ů�Ԍ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܄��ԡ���ͬ�w�ԡ��ĸ�֪���153�����M����ʾ�����ČW���a��֮���Ԅe��ĝu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Լ�Ů���ڂ��y(t��ng)��ɫ֮�����Ծ����ߵ����ݼ��гʬF(xi��n)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ƽ�Լ��ČW��(chu��ng)���@Щ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Lԇ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ƌ���ӑՓ������롣���ߴ�ǰ�ь����ƌ���Ԋ�W���`���^���C�cԏጣ���Ҋ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ƌ��Ԅe���Ԃ�/��ӛ�ĕ������`����Ӣ�İ�2000�������g��2016�꣩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P��Ů�Թ�ͬ�w��˼�����Ա���Ͽ��ء�����ɭ��Benedict Anderson���ġ�����Ĺ�ͬ�w�����l(f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Ԋ�~֮��Ů�����߂���Խ�r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(li��n)ϵ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е�ʿ����Ӣ�A��֪���_�����|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܉�ԽѪ���Pϵ�c����wϵ�ļ������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Ԋ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c���˚w����ͬһ������181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N�B�Y��ɢ�ġ�Ԓ�Z����discursive field���У������¡��@��~�R���ɞ��@��Ⱥ�w�Ĺ�ͬ�Q�^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һ�N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ߵ�Փ�C�У��@�N���w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ͬ���o���c���ƌ��Y�R�Ěvʷ�ϵ�Ů�����߂����@Щ�|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ϵ����A��ͨ�^Ԋ�Ą�(chu��ng)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˴˽��β��ɼ�Ⱥ�l(f��)չ֮�ݣ����ԋD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Y�������ض����ݣ��硰�|�ӎ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ض����}���硰����Ԋ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Y�ʬF(xi��n)����һ���棬�@һ���w����߀�w�F(xi��n)�ڌ���ͬ�r��Ů�Ե�ӛ����@Щӛ��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ἰ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ŌW�@Щ������ͬ�w��Ԫ��֮����߀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м~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ͨ�^��Ԋٛ�ā���ͨ�������Sϵ(li��n)ϵ�����189�����ڷ��㝍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ƌ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ѵ��@Щ�lĿ�H�С���ӛ�L�������С����˻���ɫ�ʣ�ͨ�^Ů��Ԋ���еĂ��w��(j��ng)�v���_�˴�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ϧ֮����

������p��
�ڡ����˵ļ����εģ�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������Ů�����x��Փ��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˵ļ����еģ�The personal is the critical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ڸ��M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ƌ��ġ����˻����uՓ�L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ڡ�����ԊԒ�����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Щ�lĿ�ʬF(xi��n)�ġ������ԡ����H���ஔ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ᵽ�������ƌ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ČW�z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ČW���u�˾���Σ��ʶ����uע֮�Z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ͨ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o�����180�C181�����@Щ�c���ƌ�ͬ�r�ڡ��ԡ�����ԊԒ���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ۼ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ƌ�ͬ�r�ڵ�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˳ʬF(xi��n)�o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Խ��ͥ�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_�ŵ����H�Pϵ�W(w��ng)�j֮����߀�ܽ�ʾ��Ů���Ļ��ĺηN�����@һ�c���д��^�m(x��)̽����
���@һŮ�Թ�ͬ�w���о����ڌW�猦���塰Ů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ӑՓ֮�����֕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ӑՓ���h�}��Ů�Ԍ������Ԅe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ҵĸ�ϵ�ƶ��µõ����_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ČW��(chu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ġ�Ů���Ļ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y(t��ng)�rֵ�wϵ�Դ��������Pϵ��Charlotte Furth, 1992�������ض��Գ��ݏ��T��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_ָ���Ļ����y(t��ng)�o��Ů�Ԅ�(chu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�Ů����Ӣ�İ�2007�������g��2015�꣩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DŮ�������Ԅe���R�ͪ����Բ�ԓ����ҕ���ߏ��U����Մ��Ů���Ļ��Ī��rֵ���ǽ�����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ߵĹ�ͬ�ۺû��A֮�����ھ���Ԋ�x���A�Ϙ�����Ů�Թ�ͬ�w����ṩ�ˌ��C��
���^���ڵ����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˃H��һ̎Փ�����ƌ����c���T��Ů֮һ��䌌Ӣ���ČW������ֱ�ӡ�Ͷ�����Ҍ��Ԅe��ƽ�����еđ���֮�顱���193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ϵ��Ԅe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ͨ�^�ı���ʽ������Ŀ���c���żܘ����Q�^���~�Ȃ���õ���ӳ���P�����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_���M���Ԅe������Ԋ����Ҋ��С�s����Ӣ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Ԅe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Ů�Եġ��M���t���~����Ӣ�İ�2005�������g��2022�꣩�����緽�㝍�J�����ƌ��ԡ��^�ҡ����ǡ����ҡ���ָ�Q�̫�壨1799�C�s1876�������Ҍ����壨1799�C1862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]�ڲ�Մ�����t��ͨ�^�@�N�P�����_���䌦�����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ğo���ƣ��191�����܌�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Y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߲�δ�����ƌ����ļ���ӡ�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µ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]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Ʒ��δ��֮�i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ԊԒ�������ƌ��x��ʮ����֮��ŵ��Ը�ӡ�������䡶�Ϛw��ӛ��δ����ӡ�������P�ߓ�(j��)���Ɯy�@�c���ς�����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ԵđB(t��i)�����P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ΏV�������ƌ����Ԅe���R�ı��_�����ஔ���X��Ƕ��������y(t��ng)���ԄeҎ(g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Ҫ��ه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ѵ��Y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ҕԊ�ŵ����ƌ��c���{�·��Đ��飨1771�C1833�������^(q��)�e������Ů���ڸ�ϵ�ƶ����Ԅe��ɫ�ı��_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ą^(q��)�e�����Ǜ�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\����С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S���]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�ΑB(t��i)��Ԓ�Z֮���Ů��ԭ���B(t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Ů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10����Ů�����ߵĄ�(chu��ng)�����c�Й�����ărֵ�^ʼ�K̎���@��һ�N�ӑB(t��i)ƽ��֮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㝍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g��·�r�����ᵽ�Լ��Ѽ�����DŮ������ϣ��̽ӑ�vʷ�ϵ�Ů�������Ԋ�����M���Ԅe���ı���/�٬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1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ڵĴ������о�������ע����ƌ����r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䡶��ѩ��Ԋ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ŵ�����(j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ͨ�^�Lƪɢ���w���Ժ���Ԋ���g���ı��Ȳ���ע�����Ч�،��@��Ԋ���D׃?y��u)��Ԃ��ԵČ��������J�������Ԍ�������㑿�������ͨ�^���N��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cԏ��߰�ʾ�ˌ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ľ��w�w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e����㑿��M�ı��е��Ԅe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g��2016�����233�C234���@�ӵ�������Ů��Ԋ�ļ��в����rҊ��
�c�����˕����Ă�ӛ�����Ԋ������M������Ů�����߃�������ĸ�ֱ��;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ұ���/�٬F(xi��n)����Ҫ�d�w����Ԋ�����顰����ʷ����interior history�����^�c����Ҋ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ӳ���Ԃ�Ԋ����Ӣ�İ�1986�꣬���g��1996�꣩�͌��e�������Ԃ��ԕ����ķ������鱾���ṩ�����w�ĸ����ܡ���һ�¡�Ԋ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Y��1743�C1819��֮��/�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͵����ӣ��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Ԃ��ԾS�ȵ�ϡ���ļ���ԁѩ�Ǹ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Y�ϸ����Y��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īI��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(x��)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٬F(xi��n)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α��ֳ��ľ���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ӵ�չ�F(xi��n)���䡰�D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ͬ�A���ڼ����е����ݵ�λ�����C��ݡ�����Ů�t֮��Գ־��P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ݡ������ܻ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δ���ݡ��Ъ��ԓ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�������B(y��ng)�ݡ��Џ��ӻ�����̓�������Ŀh��ĸ�H���@�N�K��һ���Č������`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ڼ�ͥ������еĽ�ɫ������
�eֵ��ע����ǣ������Yͨ�^���֕����M�빫���I��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ղ��õ������J�ɡ����ġ��⽻����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Ԋ���A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ӵĵط�ʩ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P��Ҫ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Ԅe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_���J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[�ޱ��_�������I(y��)�Ŀ�Ľ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ČW��(chu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̶��ό��F(xi��n)�Լ�����Ը����˳����ճ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߀���Լ���ʮ����ʮ���֮�H�x�LԊ��������E�������M���Լ����e�����ع�(ji��)��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ؕ�I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Č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Y�ҵ����ڼ�������wϵ�Ќ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҃rֵ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ڼ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N���_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F(xi��n)�ڵ�����Փ�����ϴ�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17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Ʒ�����@�N������ʽʹ��y����߀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l(xi��ng)�IJ���֮�e�܉�������ӛ��ͬ�r�ֲ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Ҵ��u֮�ӡ����߸��M���Ɯy���ϴ��o���S߀��Dͨ�^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ӛ������ɷ���V��و�ʧ���Ӣ�������ڮ��l(xi��ng)�IJ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oՓ�@�Ƿ������ij������ĽY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ϴ��o�Ĵ_������Yһ����ͨ�^�ČW�����٬F(xi��n)���ң��Ȟ��Լ��l(f��)��Ҳ���ͥ�����˻����\�Ěvʷӡӛ��
�c������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P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Y��Ԋ�Ŀ�ӡ��(j��ng)�^����ζ���L�����Խ������(zh��n)�����P������Ʒ�V��Ҋ��ǰ������Ů��Ԋ�x��Ȼ�����Ԋ��δ�܂�������(j��)��ܷQ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⌢��(sh��)ʮ���g�иж��l(f��)��Ԋ����֮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ֹ�����ԡ�����ݡ������̼����o����֪���P���ġ��D���o�ġ����134��֮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Jͬ��߀�Ǽ������~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Ů�����ߌ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đB(t��i)�ȵĴ_��ì�ܵ����@�c���r���@��Ů�ԡ��š����¡��Ġ�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P��Ȼ�����@�N���h����ԓ�����ε�ҕ����Ա�������Ů�ԲŌW�Ĕ��⡣���ض�ָ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\��1738�C1801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ČW���J����r����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Ӱ�������׃�ù������h�x�ˋD���đ���֮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\�ġ��D�W�����Ї�Ů���Ļ�ʷ���_ƪ֮������Ӣ�İ�1992�������g��2021�꣩�O����ͬ���J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f�W�\�������u��ͬ�r����Ů�ԣ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ᘌ����r���ČW���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P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б���Ů���ӵ�Ԭö��1716�C1797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Ԭ����֮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š����¡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ԑB(t��i)�ȵ������о��롶�����|����ʼ�����Đ��飬������ij�N�̶����@�ñ����Ը������ء�������Ҋ�O���˵�Փ�ġ�Ming-Qing Women Poets and the Notions of ��Talent�� and ��Morality��,�� 1997���M���y�Ժ����@һ���h���ڲ�ͬŮ���ڄ�(chu��ng)���ϵ�Ӱ푣����^���w��ݛՓ�h(hu��n)��߀�ǃA���ڌ����¡����ڡ��š�֮ǰ�ă�(y��u)�ȵ�λ��
�����ߵ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W�\ͬ�r���ĸ����Y��Ԋ�������ϳ��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顰�������Z��ƽ����Ԓ�����㌍�o�A���L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65����Ȼ��Ԋ�Wˇ�g��ƽƽ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]�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Ʒ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δϣ���c�Ŵ���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ԇ�D�ɞ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{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rֵ�����ČW�rֵ�����66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P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Y�����Ǭ�Ε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w��n)�����@�N��(w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Ĵ�h(hu��n)�����S�ٳ�����Ԋ��Ŀ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S߀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ӽ���}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Ӿ������ġ��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55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ṩ�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źõ������λ�����|���A��
�M�����P��Ҳ�����Ъ��Ԍ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δ���ڿ��e��ԇ�м��ڣ�Ҳ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ṩ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YԴ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Ƕȁ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P��Ҫ�����64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Ů�Ե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ӛ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ڵڶ�����ʣ��c�����Y������ͬ�r������Փ�������y�l(f��)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ñMТ�c�ļ�����֮�g�����б�Ȼ������Pϵ������ŮԊ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b�p���c���`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ʏ�δ��ĸ�ԵĽǶȁ혋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_��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Σ��o��(j��)�ɿ�������O�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ĸ�Č��ε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̎�����Dռ��ĸ�Ա��_�Ĭ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g���M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ʵ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ǰ��Ѹ�ٵر���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ܿ���߀���ͥ������(j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ɴˁ�����Ů�����ߵ�����㑿̷�ʽ���ɕr�������g����λ�����ˑB(t��i)�Ⱥ��YԴ�ȶ������ع�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ʬ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s��Ԫ����ò��Ҳֵ�ø��Mһ���ھ���
�Y�Z
�������o90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Ů�������о��ں�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(sh��)�ı���δ���_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P�ăɲ���־��Փ�ļ�����Writing Women in Late Imperial China, 1997��Chinese Women in the Imperial Past: New Perspectives, 1999������Ů���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ஔ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ʹ����ͬ���ܸ������ؽ��|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^�ط�ɢ���ı����l(f��)�����Ъ��ص�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2003���𣬷��㝍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c�����ྩ�D���^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�D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sh��)��(j��)�����ڴ˺�Ķ�ʮ���g������431�����Զ�҈D���^��Ů��Ԋ�ļ���(sh��)λ����ȫ���_��Ŀǰ���ڳ��m(x��)���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㝍�����S�£�Wilt L. Idema���Ͼ��С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ྩ�D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DŮ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�2009�꣩�����Ƅ�����D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ڌW��ǰ�������䱾���ߡ����^���@헇��H������(sh��)�ֹ��̵��ײ��о��ɹ������Ըߏ��U�����ض�������ČW�ߌ��Ї��Ŵ�Ů�Ԛvʷ������ʽ��revisionist��̽�����،����M��һ���µ��A�Ρ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v���TλŮ�����ߵĽ�(j��ng)�v��߀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chu��ng)�����`�ķ�ʽ����ԇ�D�����v�������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4����ͨ�^�Y�ϵط�־�������īI��Ů���ļ�֮���ʷ�������㝍���@ЩŮ�����ߡ��܄��ԡ���ԏጣ�������ČW���o�͚vʷ�Z�����p�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`�ĽǶȣ�̽ӑŮ����Α{������㑿̵��ČW������չ�F(xi��n)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c�Ԅe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ˌ�������ˇ��Փ��(chu��ng)���Ե��\�õ�������DŮ�����ķ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Ӣ�İ�߀�״η��g�˔�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^��Ů��Ԋ�ģ���һ���̶����Ƅ������A�ŵ�Ԋ�~�Ļ���Ӣ������Ă�����
�ԏġ��䱾���ߡ���Ӣ�İ憖���ԁ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W�猦����Ů�ԕ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о����m(x��)�����Ů�����ߵ��Ļ����`�䌍������Ԕ���Č��}ӑ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С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ȷքe�ġ��|���wԊ������ӛ����ӛ�ȽǶȿ���Ů�Ե��܄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µļ��w�ɹ��w�F(xi��n)��ȥ���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܄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�ڵ�Ů���c�Ԅe����Rethinking Authorship and Agency: Women and Gend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�������}�l(f��)���ڡ��Ї��ČW�Ļ�����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����һ���ؿ����£������Ԅe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ĕr�վS�����ؑ���ǰ�о������Pע�IJŌW�c�·�������(zh��n)�c�ׅf(xi��)���|�T�ă��c��Ƚ�(j��ng)���h�}��
��Ҫ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Ů��Ԋ�ļ�ҕ���Ԃ����ı����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ʬF(xi��n)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Y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Y�x������ƴ�ӵ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顰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߱��˲�����ȫһ����Ů���ڬ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Մ�������P�Ԅe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r�ֵȷ����˼��Ҋ������һЩ��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п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ӡ���^���б��Č������^�V�����Μ粻�����ˑ���Ů�Ԃ����ı����@�N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ı������c�vʷ�Z�����Ӿo�ܵؽY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ɞ���ڱ��е��о�څ�����S��ʷ�ρ�Դ�Ķ�Ԫ������֮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(sh��)�ֻ����g�đ�����Ů�Ԃ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v�̼��佻�ξW(w��ng)�j���õ�����ϵ�y(t��ng)��ֱ�^�ijʬ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ڂ����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A�ϣ����ھ��д����Ե�Ů���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˼��ȶ��Ľ��xҲ����ꐳ��£��@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õ����I����ͨ������Ů�����ߵ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






�l(f��)���uՓ �uՓ (3 ���uՓ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