���S�֣��ăɼ����θ����f�δ�Ժ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׃
Ժ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һ���J(r��n)����ƴ��_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(f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ڵ�Ī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�Ч�����ɞ麲��Ժ��ͨ�Е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@�N�L(f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δ���Ȼ�^�m(x��)�����w�S�ʵ۵ĸ�������׃����
��̫�����E���棬�H�ڡ��{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Ӱۙ����ˮ��(zh��n)�õ��^�K���S���ĸ߶��u(p��ng)�r(ji��)���K�Y�f��̫�ڻʵ����书�����y�����ĵ���̫ƽ����v֮�������ڹP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Ū���F(tu��n)��֮�С����Sͥ��(ji��n)�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䶨�ķ����d����ʸ������֮�ţ����⺲ī����M�˷�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r(sh��)ʿ�����H��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ơ�̫�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Е��o��(du��)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̫��ϲ�۵ĕ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ǰѡ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ʯ�Ĉ�(zh��)���ߣ����ˇ�m���H�мҷ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Sͥ��(ji��n)���u(p��ng)�顰��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ͥ���t���P�E��׃�������֮ʏ����ʢ��֮�f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^�ӡ���Ȼ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ʥ���ķ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S��˼���|�^��Փ���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̕�݅���W(xu��)�˱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˟o�������Ŀ�����Ժ�w����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R�W(xu��)��܊�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Ժ�w����֮���t���w��֮Դ������
�@һ�r(sh��)��Ժ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(di��n)���ġ�˾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п���Ҋһ����ֵ��ע����ǣ��˕r(sh��)��Ժ�w�����Իʵ����Ƴ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(d��o)���c�ʵ۱��˵ĕ��w���oֱ���P(gu��n)ϵ��
Ԫ�v���g���K�Y�����֣��m������M�������ƺ�Ҳ�]�܌�(du��)Ժ�w������Ӱ����@���ԏ��Sͥ��(ji��n)���K�Y�ĹP���q�o(h��)�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ϲ�I�u(p��ng)�|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ú����̕�֮�Kī�߶ȣ����M֪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̕����Kī�߶��c�K�Y���L(f��ng)��Ȼ��ͬ��
�@�ɼ����γ���ĸ���s���V�҂����@�l·���ƺ���δ���m(x��)��ȥ����׃�����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Ż��ڻʵ�����Ѧ�ס�������ʯ��Ԋ���Ć��l(f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Ԅ�(chu��ng)�ݽ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ݽ���׃���ɵ��Е����ݕ���һ�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Ķ�����Ŀ���@λˇ�g(sh��)�ʵ�Ҳ��(du��)ʿ�˕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r(sh��)�˲̽{�ڡ��F��ɽ��Մ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Sͥ��(j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Գ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ڕ����ƺ���(du��)ʿ��Ҳ��Ӱ푣��ڲ̾����̱����Ʒ�У�Ҳ�����ҵ��w٥�ĺ��E���@Щ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˻ʵ��cʿ�˕����ľ��x��ͬ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ҕ�XЧ���ϣ��w٥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L(f��ng)�е��K���S���ו��L(f��ng)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dɫ���߂亲���̕��L(f��ng)�ėl����
һ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猎���꣨1104�����£���λ���õĻ����ؽ��ˡ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Ⱥ����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Ȉ�(z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У����ξÏU���w٥�O(sh��)�Õ���Ժ�����B(y��ng)���ҵ�ͬ�r(sh��)��Ҳ���B(y��ng)�`���t���Ĵ�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ЈD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͢���ԈD�L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һ�w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֮��Уԇ�s����֔(j��n)�ɕ�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ʽһ�������Գ猎���ӱO(j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ǡ��Թ�������С���鷨���`�Զ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О鷨�������²�����֥���w�鷨������ԇ�t���Է��A�����m�У��h�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퍹ţ��϶����מ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ЈA�P���A���з������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w�ߞ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܈A���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ģ�¹��˹P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^���¡���
ֱ������Ԫ�꣨1126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˶�ʮ������ȫʢ�r(sh��)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_(d��)500�������ڛ]�����B(y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ʷ�Ľܳ��˲ţ��܌��������J(r��n)����ڡ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O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̓�ٷ��s�ķ���c(di��n)�Y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ǿ�����Ҋ�����w٥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롰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ָ�c(di��n)���Pī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Ȼ��
�����Ͽ�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(hu��)�ɞ��Tλ�ʵ۵��̕����t���҂����P(gu��n)�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ĕ�ˇ��Σ�?j��)��θ���֮�H���w٥���L(f��ng)��(du��)����Ժ�w�����Ƿ�߀����Ӱ���
�@�ο�r(sh��)�Ƴ��ăɼ����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҂���ʾ�˚vʷ����ò����˾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Т��Ǭ�����꣨1165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Т�ڴ������꣨1176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(zh��ng)�hӲ�����ٕ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ϣ������ț]�Ђ��y(t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֮�L(f��ng)���Ժ�w���E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˕����ǘӡ����⡱������Ҳ�]�и����w��(g��u)��Т���w�Y�ĕ����wò��

�����w��(g��u)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Т���w�Y���w��Ԋ��
�ڴ������δ����E�������Ժ͡�˾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͡�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ȵ����ǡ�����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1114�꣩��������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꣨1114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Ф�w٥���ͻ����H�P���}�ĕ�(hu��)�D���й�֮ͨ̎���w��(g��u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(f��ng)�s�]���ڃ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Ҋ���ڕ��L(f��ng)��(du��)���γ���Ժ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r��n)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(di��n)�����J(r��n)���@���ǻ��ڽ��ƕ��W(xu��)�ɹ����w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߾��DZ������{(di��o)�̳����ĕ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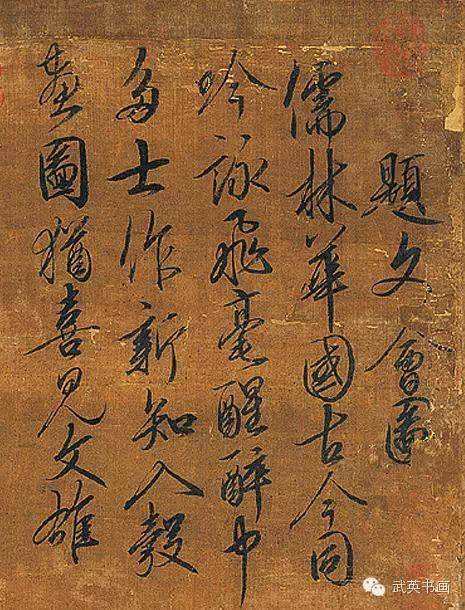
�w٥���}�ĕ�(hu��)�D�����_(t��i)���ʌm����Ժ��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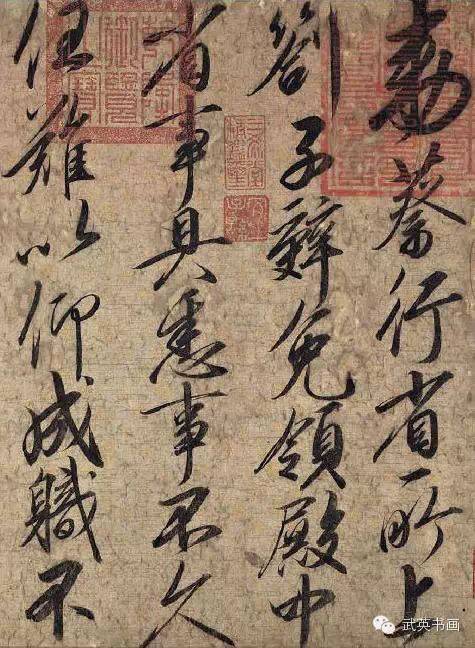
������뷾������ֲ������|��ʡ�����^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뷡��\(y��n)�P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ˮ��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�һ�o������ǰ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ɼ����θ����mȻ���w���L(f��ng)��һ�£������ùP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Щ�µă�(n��i)�����҂����ԏ��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ʥ�̡��ùP��Ӱ������M�۵ij��ǣ��Q�^�ij��h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c(di��n)�ĺ���(y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Щ�ط�߀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ڵġ��n�_힡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H�ܵ��˻��ڵ�Ӱ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ڕ�Ժ���x�С��`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du��)��(y��ng)���ùP�ͽY(ji��)�����c(di��n)���y(t��ng)�I(l��ng)�ڡ��Է��A�����m�����h�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퍹����϶����מ��ϡ��ĸ��{(di��o)֮�¡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m�Y(ji��)���ùP���w�c��˾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쾚�ϵ�������֮һ�ɵĹP���Y(ji��)���c���ڵĈ@��Y(ji��)�ϸ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˶��⣬�ֵĽY(ji��)��(g��u)���ùP߀�и߶ȵ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@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ͬһ���t֮�֡��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ʮ�����w�F(xi��n)���@λ���t�����ϵij����c�M(j��n)�����ĕ����r(sh��)�g���Ɣ����@λ���t������ڕ��W(xu��)�r(sh��)��o(j��)���p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r(sh��)���ǹ�ϡ���܉�ѻ��ڈA����Е����͡�����ʥ�̡��Y(ji��)����һ��Ҳ�����κ��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Ҋ�@λ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IJ��ܴ_�пɷQ��̎��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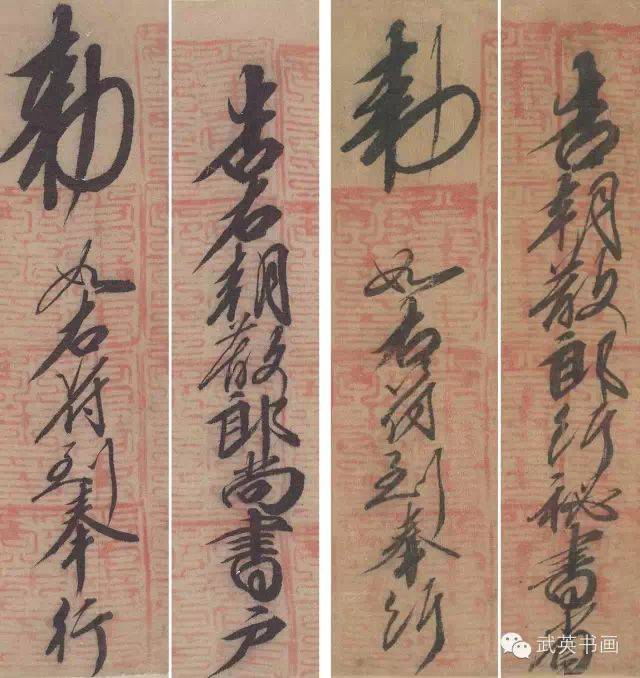
��˾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ң��ֲ�








�l(f��)���u(p��ng)Փ �u(p��ng)Փ (2 ��(g��)�u(p��ng)Փ)